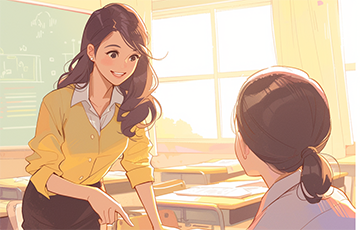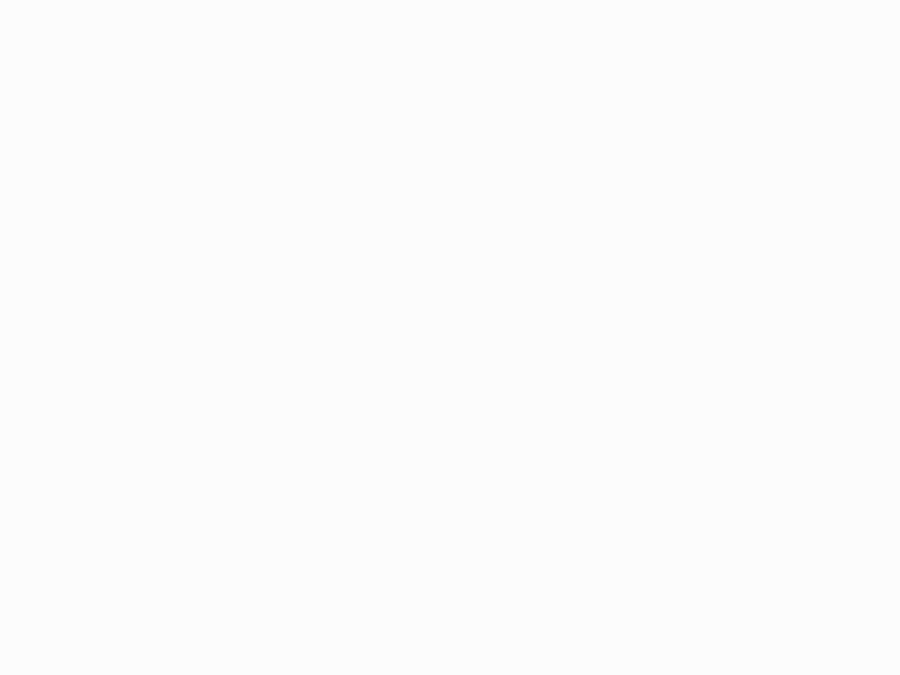我知道,有个诅咒,横空出世一般,将降临到我的身上。 -题记
前世
断头台上,5尺钢刀疾风而下,女子闭上了眼睛 。
我是郭箢,从小在江南长大,和一大家子三姑六婆一起生活。说是三姑六婆也不过分,因为在这偌大的郭府之中除了帮工的用人之外就几乎全是女眷。从小的时候起就总是听父亲叹息说什么郭家后继无人,香火断了之类的话,听到这句话的我很不服气,从躲藏着的草堆里蹿出来,直冲父亲嚷嚷。而父亲也只是用怜惜的目光望着我,拍拍我的头顶,然后久久无语。我知道,父亲还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。男儿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可以更好。于是从那时起,我就暗自下了决心,男儿能做的,我一样能。把自己在书房里关了三天,害得父亲以为我生了什么病,从镇里传了大夫。
一晃十载,我已是一个立箸为芨的少女。我到了该嫁人的年纪,镇上年纪相仿的小姐们几乎都嫁了人。十载光阴我致力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,可是如今,再怎么的才华也要嫁到人家去了。望着那成叠的朱红喜帖我发了愁,耳边回响起父亲曾经的话,“若你是个男子,定能效忠朝廷,助皇上一臂之力。”心忽的浮了起来。
趁着夜色,一个人影翻出墙外,快马驶向长安。
一月之后,金榜高挂,那榜首少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。
“你知道吗?”一个手拄拐杖,步履蹒跚的老妪颤悠悠地说道,吊足了人们的胃口,“听我儿子说,那状元郎才15岁,答题之时一挥而就,那气势……”
两小儿打闹,败的那一方站起身来,朝另一儿递去鄙视的目光,“谁要跟你打,我回家好好读书,明年像郭芫一样考状元!”
西街茶馆里说书的艺人折扇一展,“话说那新科状元郭芫……”
……
我倚在长楼南面窗口,长安是个好地方,可是家中父亲……再者我本是女儿身,又怎么瞒得下去……风沙漫天,一粒沙子入了眼,泪如陨星般划破厚重的妆。
“小姐哭得好伤心,不知在下可以帮什么忙?”我倏地一惊,收起泪水,回过头去。“你,公子你在说笑吧?这儿没什么小姐,只我一人,莫不是公子你闪了神?”
抬起头才注意到是个锦衣罗缎的青年,约莫20岁,已加了冠,眼里透着狡黠的光:“那请问公子你如何会打耳洞?新科状元好奇怪的雅兴啊!”
第二天,皇上昭状元入殿。把我从长楼客栈接入了宫。车上我掀开帘子,望见的是长孙侯细长深邃的双目,顿时就吞没了我。殿上皇帝要封我作官,我说我只是个女子,应试是儿戏之举。皇帝龙颜大怒,殿上百官俱俯地上,霎时间只有皇帝的怒吼回响在朝野。
欺军之罪,按法当诛。我只是觉得对不起父亲,若是我当初安分,嫁了人,做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人,生个一窝孩子,也就不至于这样。p分页标题e
三天后,我被推上了行刑车,满城百姓议论纷纷,有惋惜的,也有幸灾乐祸的。惋惜的是我一身才华,幸灾乐祸的是我是个女子,不自量力。
长安城中风沙漫天,长发散开,在风中飞舞,像妄意滋生的野草。
我不怪谁,只怪我生错了空间。
我发誓,下一辈子我一定当个无才的女子,安安稳稳地过下去。
今生
余家大院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声音之洪亮,让院外的那只狗精神一振,一起吠了起来。接生婆诌媚地笑着,揭开婴儿的襁褓,指着一块胎记对母亲看:“瞧,是个状元胎。”母亲只是憔悴一笑,接着睡去。
转眼间,我到了初三,先前的日子好似在怨恨我无端将它们花去,一齐从时间的那头涌出找我算帐。而我似乎也亏欠太多,无法补偿。
于是我索性不去管它,变本加厉地挥霍它。日复一日,我逐渐变成了一个皮肤苍白,面目尖削的女子,阅读、音乐成了我生命的全部。
音乐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镇痛剂,对我而言,它像一个可供一只四处流浪常常受伤的野兽藏身的洞穴,我可以在里面舔舐我的伤口。朋友说她可以在音乐里自由飞翔,一直飞过太阳飞过月亮,飞过沧海泱水四季春秋,飞过绵延的河流和黑色的山峰,飞到乌云散尽飞到阳光普照。
我想我没那么自由,我只能在音乐中将身子蜷缩得更紧,我好沉沉睡去,睡到睁开眼睛一切烦恼都不见。
那样我就会很快乐,就不会在黑夜里一个人流下眼泪。
阅读似乎是我生命中极重要的状态,像午夜里的御风飞行,黑色的风从翅下穿过的时候,我感到莫名的兴奋。我看的书总是很极端,或许我天生就是个极端的人。
时常上网,躲在网络背后写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,编一些支离破碎的谎话。掌心空洞,悲悲戚戚。站在空城之中,找不到出路。
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未来。
后怨
现在是公元3006年3月19号,我是一个刚从娘胎里分裂出来的浮游生物。我没有大脑,没有思想,我快乐地生活在这世上,没有哀伤。忽听一阵嗡嗡的响声,我被吸入了吸尘器的无菌箱中,失去直觉。
茫茫宇宙之中,我突然明白。
有个诅咒,他说,你是每个时代的悲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