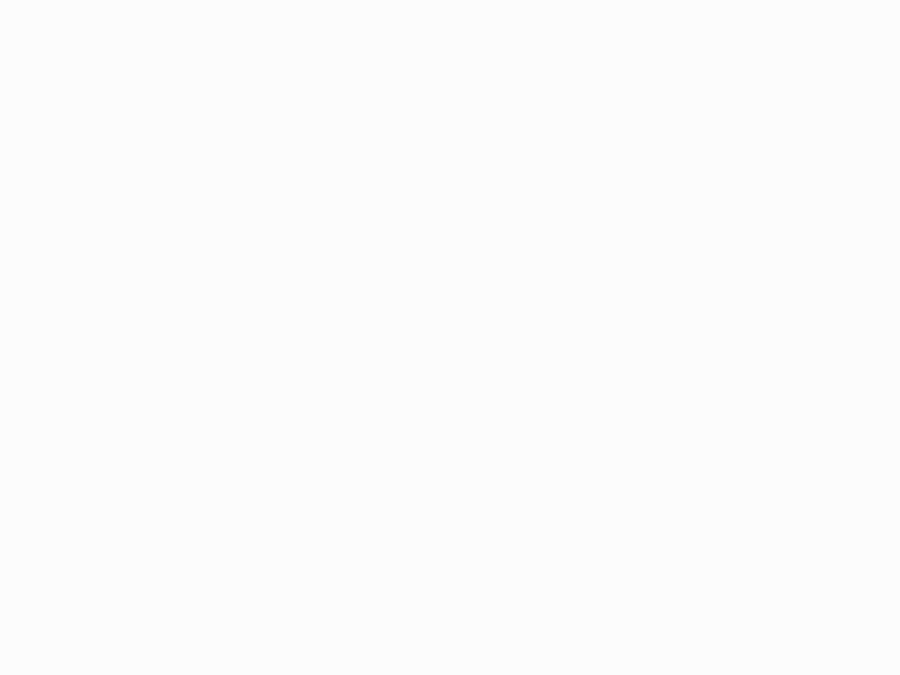我是在蓑草连天的二月回去的。
本来纯粹只是回来看看,却未曾想到:它已是这般沧桑了。原本结实的土墙貌似已坍圮地有些时日了。青砖却依然是青砖,苍苔来此安家。黑瓦却依然是黑瓦,向后退了几十步后,猛然发现:飞檐没有向上勾起,只是懒懒散散地卧着。真的很想握着铁环在门上重重地叩响。又有谁会握着锈迹斑斑的东西做这些傻事呢?我的勇气只限于抚摸着苍白支离的门神像。
轻轻一推。门,是虚掩着的。
呵,我的故事,我与老屋的故事原本也是虚掩着的。门后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我有一匹“战马”。前蹄起,后蹄落,四蹄着地很是平常,却不能凌空来一个飞跃。骑着长凳,环游一周。板凳“吱呀呀”地呻吟着。系上一串风铃,随风飘荡,好似断桥边秦琼与杨林斗智斗勇。红漆一块块地脱落下来。早早地,地上已经被磨出了几个深深的坑了。
一个踉跄,不禁惊醒过来。看着脚下的大坑,我只是一直“嘿嘿”地傻笑着。它是这样结实,已被我牢牢地踩在脚下了。老屋毕竟很久没有来过了。它没有落地窗,更没有天窗,但我仍能感到蛛网密布的深处是那熟悉的灶头。
伸手,又回到了那个世界。拾柴,加火,炉灶里被我塞满了一膛松树刺。噼里啪啦的火炉中,疯狂地炸响着。柴木的尾部“嘶嘶”地翻着水泡,炉灶深处的水似乎被热气逼迫,节节败退。脸好烫,我仍然自顾自地添着柴。祖母奋力地炒着,一边招呼我这个小滑头慢点。但把菜烧焦一向为我所乐。我是如此向往烈火。无论是通红的底炭,还是牵连着薄烟和烈火的柴薪,都竭尽全力地配合我。一切热都将最终聚焦在明亮亮的炉膛和黑乎乎的锅底。欢笑,彻底地使坏,彻底地欢笑。
再往里走些,应该有一口大锅了吧!我醒来后喃喃自语。相比刚才的锅,应有小巫与大巫之分了!
喜滋滋地畅想着在锅里洗一次热水澡的情景。身下是热气腾腾的温水,再下面是一口直径数米的大锅。再往下,就不得不是熊熊的烈火了。原始而又古拙的洗澡方式,仍然是畅快淋漓的。浮游于江海之上,幻想着烹杀活人的古事,莞尔一笑,不也是人生一乐吗?四周紧闭似是囚笼,一张门帘隔断东西。热气在这四方的空间内翻腾着。啊,美哉一浴!
老屋陈旧事,我又怎能不动心呢?这是我曾经倾心的圣地,是扎根生长的土地。我是一根芦苇,有思想的芦苇。虽然蓑草连天,但芦苇依旧。
心中空落落的,尽力去抓住我与老屋的最后一缕记忆,不至于随风逝去。
以上是我与老屋的故事。
掩门,给故事一个大大的句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