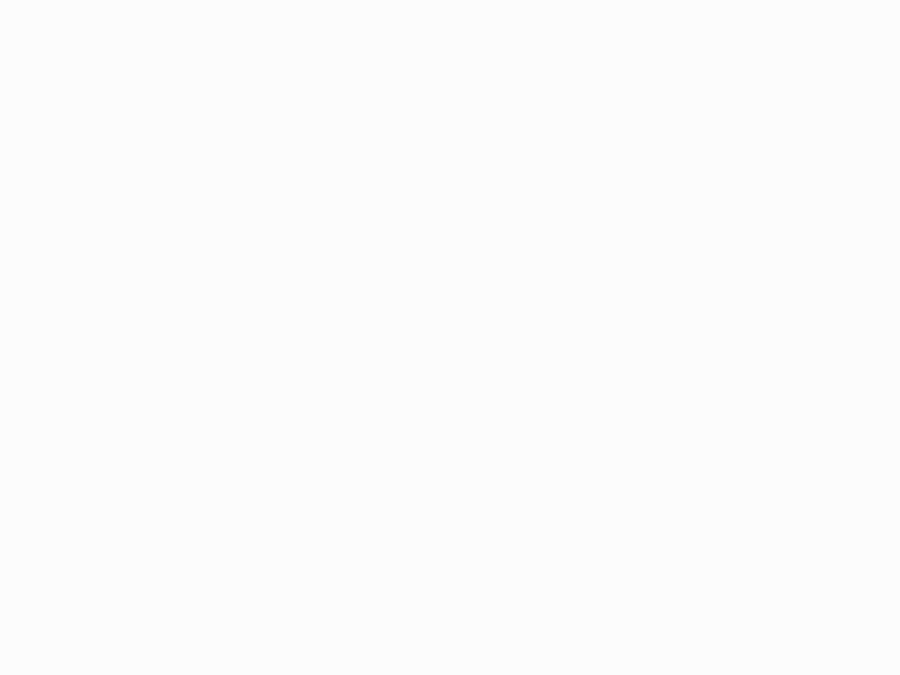——让悠悠来告诉你:有一种快乐不需要理由
穿过窄窄的村中小道,滚落在眼前的是一扇古老,却已败落的院门。墙角有那么一棵茂密的枇杷树,树下卧着一只光滑的大水缸。一颗颗鹅卵石镶嵌在泥地中,一切都在暖烘烘的日光下打着盹,像有人在哼着一首催眠曲。
她是悠悠,我刚满一周岁半的小侄女,住在外婆家的隔壁。
慵懒的阳光被乌黑的瓦片裁成两瓣儿,悄悄地粘在悠悠的脸上,捞起两朵粉嫩粉嫩的火烧云。陈旧的木门被风挠得痒痒的,“嘎吱、嘎吱”地笑。悠悠不知是为什么,也笑了,笑得像春天里含苞欲放的花蕾,仿佛会在不经意间,绽放一朵最娇艳的花朵儿。两瓣儿阳光这下儿可挂不住了,从悠悠的脸颊上滑落,兜在那个缀满了花边的衣角。悠悠垂下脑袋一瞧,更乐了,拍着云朵般的小手,在原地蹦跳起来,起起伏伏的脚跟,敲击着泥地,是曲悠扬的小调。突然地,像那滚落叶间的露珠似的,阳光也滚落了,在地上撞碎了,拼出了一幅优雅的碎花图。悠悠伏下身子,认真打量着那一群被“聚光灯”打亮的蚂蚁兵。“虫虫——虫虫——”地不间歇喊着,眸子里尽是对这些小虫子的喜爱,嘴角又不自觉地向上勾起,仿佛下定决心要与新月的弧度比个高下。
“呜——”旧水壶的鸣叫声划过空气,与此同时响起的是舅舅、舅妈(悠悠的外公、外婆)的声音——“悠悠,该洗头了”。 顷刻间,像按了“OFF”键似的,悠悠的笑容就收敛地一干二净。我对悠悠同志抱有十二万分的同情与理解,你想啊,洗头时,你得一动不动地躺着,还得忍受一只大手对头顶那片“净土”的侵犯,头上常常顶着一轮明晃晃的太阳,让人看得发晕。最后,还得在吹风机下,接受热风的肆虐。这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。
可是这也是件没法子的事。悠悠一会儿就被舅舅、舅妈拉上了“刑台”。算了,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吧。悠悠马上又学会了其中的“享乐之道”。不能动是吧?我悠悠偏动,我把脚丫子当做快板,互相撞着玩,你能拿我怎办?太阳晃眼?我就乖乖把眼皮盖上,让眼珠在底下不停地“噜噜”转。我还要把所有的牙齿露出来,让它们和竹匾上的笋干一样晒太阳,和太阳比比谁更灿烂。于是太阳越来越猛,悠悠越笑越甜。最后,舅舅、舅妈一开心便赦免了最后一关,让头发在太阳下自然干。
悠悠从舅妈的怀抱里一挣脱,便跌跌撞撞地跑开了,一头的水珠被洒落在身后,在阳光下更晶莹剔透,犹若一张张烂漫的笑脸。
悠悠在她的无忧城堡中似乎永远快乐,因为她的快乐是那么廉价,不需要任何理由。